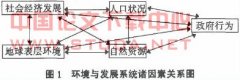离死亡还很远,社会主义依然保持其最初的合理性——它的任务是抵抗起因于全球性资本主义固有的不稳定和自我毁灭系统的不可避免的危机而引发的法西斯主义、故意伤害和野性。——特里・伊格尔顿占卜者力图预言未来是为了控制它。他凝视入一个社会系统的内脏以便解密预兆, 并向它的统治者保证他们的赢利是安全的并且系统将忍受。在当今社会, 他一般是经济学家或商业主管。先知, 相反, 没有兴趣在预言未来上,他会警告人们改变他们的方式,不然不会有未来。他关心的是谴责世界的不公道, 而不是梦想一些完美未来; 但因为没有某一正义的概念您就无法辨认不公道, 在指斥中已经暗含了一种未来。
不是以某种方式连接现在的未来会是难理解的, 正如一个跟现在完全相同的未来会是不受欢迎的。中意的未来必须是可行的, 否则我们只能无用地渴望, 象弗洛伊德的神经病患者,因渴望生病。但如果我们简单地从现在读未来, 我们取消了未来的未来性, 就像新历史主义倾向于删掉 过去的过去性。严重异常的乌托邦分子, 以他的头坚硬地插入沙子, 是顽强的实用主义者,他们相信未来会比现在更美好。这美好的错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拉德比特、巧克力曲奇饼会永世长存到5000年,使那些预言大难来临的人显得很没有脊梁骨。不管福山怎么认为, 问题不是我们可能有太少未来, 而是太多。我们的孩子可能居住在有趣的时代。
这是高度可能的, 在以后的十年将是资本主义的一次主要危机, 这不是说它是确定的,或将变成社会主义。未来一定是与现在不同,不保证它将会变好。但是当西方把它的无盖货车引入越来越不透气的圈子和关上舱口盖,它的人民越来越被疏远 , 被偏移 , 被剥夺 ,越来越排外(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 并且当市民社会由根部被撕毁, 它不需要诺查丹马斯就可以预见马上降临的动荡景象。
没有很多社会额外雇工,您无法让市场力量前进, 否则您要冒许多不稳定和怨气的险; 但就是超雇使市场崩溃。系统破坏它自己的霸权, 没有必要左派从中作梗。我们并不担心历史仅仅将重覆自己,而是担心当左派涣散、不成组织,没有力量对生产方式构成自发性反叛时,它自己已开始分裂。然后造成的问题是,更多的人会受到伤害。
这是更加遗憾的,当您回想起左派的提案是多么的谦虚、有节制。所有它想要的只是大家在这个行星上能够吃和有工作、自由、尊严等等。如果要发动一次革命来达到这个目的,就说明现状是多么的可怕。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极端主义, 不是社会主义。 理想主义的最喧闹的形式不是社会主义, 而是认为只要给足够时间, 资本主义将哺养世界的信仰。我们究竟要给多少时间来证明这个说法最终是荒谬的。
我未被说服, 虽然如此, 象悲观和乐观这样的术语仍然有政治意义。什么事关键?- 什么的确是任一卓有成效的道德或政治行动的必要条件?- 是现实主义, 有时带领您走向愁苦,有时是欢腾的。现实主义是非凡艰巨的。关键是要为正确的原因感到忧心忡忡, 这是左派有时弄错的地方。如此让我简要地明白解说一些左派不必沮丧的原因。
首先,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认为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左派的当前的危机是没有任何东西做。很少社会主义者由80 年代末事件不会有所醒悟, 因为幻灭是以幻想为前提的。上次, 西方一大批知识分子充满幻想是在30 年代对前苏联, 确实已经过了很久。的确, 如果您想要那个系统最有效的批评, 您需要的不是西方自由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主要潮流, 比艾赛尔・柏林总是有更根本的对斯大林主义的抵抗。在任何情况下, 全球性左派早已处在深刻的危机中,在第一块砖被从柏林墙撞出来之前。
如果说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有一个原因左派应该感到沮丧的, 更多因为那崩溃展示了的强大的力量资本主义(通过故意地毁灭性军备竞赛, 是导致苏联倒下的主要原因) ,而不是因为某种珍贵的生活形式消失了。即使如此, 在80 年代晚期发生的事情是一次历史逆转, 带来所有它的可怕后果。这个逆转不应该发生在80 年代。
亦不是平民的对此的冷淡反应足够真正原因愁苦。那主要是因为这是神话。那些喧闹反对难民和要求用中子炸弹保卫他们的物产的人也许不文明, 但他们不无动于衷。有许多好公民在我居住的北部, 爱尔兰,都很有同情心。人和妇女通常是只无动于衷于对他们无动于衷的某些政治。人们也许当前不怎么考虑政治家或剩余价值理论, 但是如果您让高速公路通过他们的后院或关闭他们的儿童的学校 , 他们将足够快速地抗议。并且为什么不 ? 它是合理的抵抗不公道的力量,如果你这样做没有许多种风险并且有成功机会。这样抗议也许是无效的, 但是那不是议题。拒绝根本政治变动 是还合理的, 在我看来,只要系统能付得起您一些称心,虽然 贫乏, 并且只要选择对它依然是存在的。无论如何, 多数人民投资太多能量在简单地生存, 在直接物质事态,留下太多空间给政治。但是对合理性的要求在今天意味着什么? 在18 世纪90 年代它意味着去除路障。而且, 一旦一个政治系统停止能提供足够的称心让它的公民对它忠心, 那么只要一次合理地低风险, 现实选择涌现, 政治反叛当然是一样可预测。种族隔离的结束是这类事发生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信号。
没有证据表明全体公民是迟钝或满足的。相反, 证据表明他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相当不安; 然而, 面对巴西无土地运动, 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美国学生反血汗工厂游行, 无政府主义袭击财务资本主义等等,你无法夸大左派的缺乏抵抗状态。
关于工人阶级消失的论文也经不起详细考究。它是真实的, 无产阶级在大小和重要性上的意义上收缩了; 但下层劳动者, 在工业体力劳动者的意义上, 还不是与工人阶级一样。您还是工人阶级,并不因为您是侍者而不是服装工。大略地说, 下层阶级表示一种劳动力, 而工人阶级则表示在生产的社会联系之内的一个位置。(它部分是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几乎完全相同导致这种混乱出现了。) 总之, 无产阶级, 这个概念在严格的技术意义上,在全球性条件下绝对增加了。认为它在全球化条件下相当其他阶级缩小了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不存在一个必要条件即要求工人阶级必须是 多数人 社会阶层才有资格作为革命代理。工人阶级作为最普遍的阶级不因为它是最众多的, 而是因为对它来说达到正义意味系统的全球性或普遍变革。
亦不是说工人阶级一定是最凄惨和孤苦的人群。有大量人- 游民、年长的人, 和失业者(我们或者叫他流亡知识分子) – 情况更糟。工人阶级由一些社会主义者看作革命代理不是因为它遭受很多苦(它有时有, 它有时不), 而是因为它是安置在资本家系统之内因此从可行性上说 能接管这个社会。象其它基础力量, 它同时是在那个系统的根和源泉并且不能完全为系统所吸收, 它是系统的逻辑的一部分又是它的颠覆力量。如果说工人阶级, 对马克思主义来说, 有一个特别功能, 不是因为它是特别凄惨或人数众多的, 而是因为这是, 在弗洛伊德意义上,象征性的, 代表矛盾, 象一个领域的边界, 既是里面也是外面, 体现某 系统整体上的双重或矛盾的逻辑。
在古老世界 无产阶级' (proletarius 用拉丁语) 指那些 生产孩子服务国家的人( 制造劳动力) 因为他们太穷以至于不能用物产服务它。无产阶级, 换句话说, 是在性的意义上与作为物质生产力量是一致的; 并且因为性再生产的负担主要在妇女, 没有夸张地说, 在上古世界, 工人阶级是一名妇女。 的确, 它今天越来越是这样。地理学者大卫哈维 讲到未来的对抗力量是女性化无产阶级' 。先进的资本主义使在社会主义者和男女平等主义者之间那些惨淡的老争论越来越多余。资本主义将社会主义者和男女平等主义者推入彼此的怀抱。(我隐喻地讲话。) 当然, 这些对立力量也许失败。但如果他们首先就没有存在就完全是另一回事。
左派应该是阴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后被抹黑? 不, 因为它没有。它被击败了, 但那是一件另外事情。称它“失去名誉” 就象称莫桑比克没有名誉因为它由葡萄牙人曾经拥有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在苏联倒下时失去名誉抹黑, 那么为什么它 未失去名誉,在60 年代和70 年代, 当我们已经知道苏联是一种怎样奇怪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未被撕下假面具,没有在智力上破产; 部分因为它不需要 。 整体文化和政治转移已经将作为实践力量的它甩在后边, 但几乎不反驳 它作为世界的描述。的确, 作为世界的描述, 什么比1848 的文件更中肯(共产主义宣言), 预见未来传播的全球化, 加深的不平等, 升级的不幸 和战争增多? 这比起梅纳德 凯恩斯的理论肯定很多较不过时。
在任何情况下, 当人们称马克思主义失去名誉或没有合理性, 往往表明他们只知道马克思主义思是什么。虔诚的反基础论者反复讲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虽然我们完全可以对他们的信条的本质作些分析。但说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信条是不容易的问题。关心阶级? 一定不是: 马克思和 恩格斯 坚持, 这绝不是他们的发明。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私有财产的废止, 人的合作、社会平等、结束异化和市场力量? : 许多左派分子分享这些见解没有因为马克思主义 ; 威廉布雷克, 例如, 分享了几乎所有这些观念; 雷蒙德威廉斯也是如此, 但他没有称自己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经济决定? 很好, 或许有所接近; 但西蒙德 弗洛伊德, 他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朋友, 坚持认为社会生活基本的动机是经济 , 并且没有这烦人的强迫我们整天会无所事事。历史不同的物质阶段 确定社会生活的不同的形式? 很好, 这几乎是启蒙主义的常识。
是社会主义的生存, 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更重要; 虽然也许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主要载体,一方的生存不可能离开另一方。对马克思主义来说,什么是特别的,是关于一个生产的历史方式改变为另一种的机制的一种相当技术化的理论。如果工人阶级将来上台, 它是因为这是那个机制的逻辑结果。但您可以相信前者而没有相信后者。马克思主义经常被作为理论和实践同一的学说; 但非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可以不遵守理论却能支持马克思主义者 的 实践。所以说这种说法需要重新检验。在上个世纪, 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经常做了一些马克思提倡的事, 譬如推翻资本家社会联系。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社会主义也没有在理论的意义上破产,从它未被清除出思想地盘的意义上说。在这个领域中有大量的好的左派的理论:有很有启发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图景的著作, 有关于市场的功能在何种意义上还可以走多远, 等等。有人可能增加, 同样, 20 世纪没有目击革命冲动的失败, 仅仅地址改变; 在它的中间十年它最狂放地看到了现代世纪 反殖民主义 的根本运动的胜利, 将老帝国最后从 他们的位子上赶下。社会主义被描述为在历史中最巨大的改革, 而反殖民地奋斗肯定是其中最成功的。
不, 以上所列的原因绝非无精打采的辩护。亦不是信仰 资本主义系统的坚固。一些醒悟的激进分子也许持有这个观点, 但IMF 一定不会。它相当意识到整个系统病态地不稳定。并且 全球化加深了不稳定; 如果世界的每一点儿牵连其他点, 那么一个点摆动可能意味另一点痉孪,第三个点则是 危机 。
然后什么是左派应该感到担忧的? 答复肯定是显然的: 不是系统的坚不可摧,而是它太 强大 有力- 对于当前的我们。这是否意味着系统会永远持续? 它最终会止步不前,不需要它的政治对手的帮助。这是否是好的或坏消息,尚无定论。不用社会主义带来资本主义的毁灭; 资本主义毁灭自己; 系统一定是能自杀的。但它需要社会主义, 或相似的东西, 使系统不会将我们全部带入野蛮时代。并且这就是为什么对立力量很重要: 尽可能的抵抗一定从系统的主要危机中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打斗流血和野性。瓦尔特 本杰明明智地观察, 革命不是出轨的火车; 这是紧急制动器的应用。社会主义理论的功能是, 保护还未诞生的未来: 它提供的, 不是风暴, 而是当代历史的暴风雨中的风雨棚。